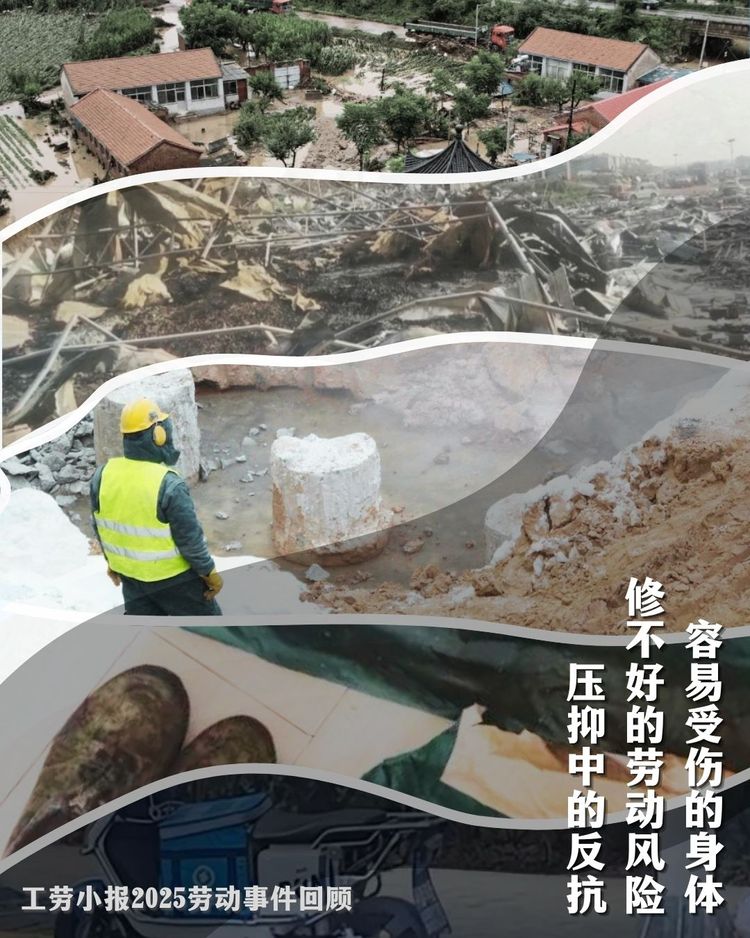【年度专题】劳尽一生,何以为安?——工人养老问题分析与访谈

专题介绍:为何要研究工人养老问题?
清晨的街头,年迈的清洁工拖着扫帚走过;夜深时分的小区门口,头发已斑白的保安独自守着大门;工地上,年过六旬的建筑工仍在吃力地扛着砖块......许多本该在晚年卸下重负、安享生活的工人,仍被现实所迫,继续出卖劳动力。他们大多从9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城市打工,在流水线上忙碌,在建筑工地上流汗,在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中耗尽了青春,也撑起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然而,为何劳动者们仍无法在晚年退休安定呢?他们为何没有被社保系统接住?他们的养老金为何没有使他们不用再劳作?养老保险,原本是劳动者的基本保障,却被政策的变化、企业的逐利和政府的不作为割裂得支离破碎。从工厂里的“退保风潮”,到“临时账户”制度,再到补缴社保的重重阻碍,甚至今年的“延迟退休”政策,我们一次次看到年老的工人们被推向了一个没有退路的死角。
我们要关切的不只是个别工人的辛酸,而是整个社会养老保障系统的扭曲。在政策的语言中,社保被描绘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福祉,但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对工人薪资的预扣和延迟支付。然后,它也像许多工人遭遇的工资问题一样,被打折、被拖欠、被克扣。
这一切又不仅只是政策设计的缺失,它与整个经济生产体系密不可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和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工人的未来“外包”给了市场主导的养老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社保的“市场化”不仅未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反而让大多数底层劳动者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资本和政策之间的合谋,最终使养老保障成了一种隐性的剥削机制的帮凶。
此次工劳小报的2024年度专题,前后总耗时5个月,试图从历史沿革、政策缺陷、现实问题、斗争历程、工人访谈、反思展望多个层面,全景式地深究工人养老问题。
我们希望揭示:是谁从工人的养老金制度变化中获利?是谁设计了这样的规则?又是谁默许了它的执行?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压在工人肩上的现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记录,为工人抗争提供一些历史的线索和实践的经验。因为许多曾经为了补缴社保、捍卫自己晚年生活而愿意发声抗议的工人,仍然不愿沉默,也希望这些故事被记得。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这篇专题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很长——因为工人养老的困境就是由这样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相互纠缠而成的。这是一期不容易阅读的专题,也充满了大量历史的回顾和政策词语。但我们希望拜托每位读者,试着留出一些时间,耐心阅读这些文字。你或许不必一次读完每篇文章,或许当你留下一个对工人养老的印象后,会再来重新翻看余下的文章。但我们诚恳地希望你能最终读完全文。我们也希望你在阅读时不必被这些沉重的现实纠缠住,或许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但至少,我们可以重视社会保障政策,作为现在和未来的劳动者,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个社会应对我们的晚年生活给予合理保障。
分析:社保政策变化、关键问题与现实的遭遇
要社保:工友养老斗争的历程
这篇文章综合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工友维权协助者以及多个历史材料的信息,粗略整理了广东地区工人养老斗争的过程。1990年代,随着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工厂,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然而,由于当时社保政策滞后,政府部门对社保政策宣传不足,许多工人对社会保障的概念知之甚少。同时,企业普遍逃避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以及政府部门执法不到位,甚至引导工友退保,导致工友退休后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2010年新的《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广东地区多个城市的工人们开始集体行动,通过仲裁、行政诉讼、直接维权等方式要求企业补缴社保。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面临着重重阻碍,包括企业拒绝承担补缴责任、滞纳金负担过重,以及政府部门在具体执行上的踢皮球。2017年“临时账户”的设立带来了新的问题;同时2019年社保征收权移交至税务部门后,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使得社保补缴的程序更加复杂化,工人们的养老权益争取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历史回顾:从工人参与分配到被裹挟
在这篇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历史回顾中,我们希望去探究:
- 养老政策与其对应经济体制的关系是什么?
- 在各时期,养老制度本身有哪些特点和问题?
- 这些不同的养老制度变迁对于劳动者意味着什么?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会不断地加强经济关系的再生产。理解它的变迁和内容本身,不仅是理解其设计是否合理、条件苛刻还是宽松、待遇是否令人满意,我们还需要理解它与经济体制间的关系。我们也并不想对不同时期的养老政策做出道德上的好坏评价。事实上,历史前后的不同政策根本无法直接比较。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读者从沿革中窥见国家、经济制度、市场、阶级斗争等这些复杂维度间的关系,以及其对劳动者的巨大影响。
在1951年至1977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采取“国家-企业”模式,由企业承担保险费用,劳动者不需个人缴费。这一时期的养老制度除了需要承担劳动者老年生活保障外,还需要遏制私有制复辟,因此强化了劳动者总体在经济分配中的地位。不过,受限于计划经济的不成熟,此时期养老金制度存在资金管理分散、发放不稳定等问题,各种工种、阶级成分、户籍的划分也让其在分配中显得不够合理。
1978年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随经济体制的转型发生根本变化,劳动者被纳入缴费主体,逐步形成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分担的统账结合制度。此后,养老制度引入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 和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试图通过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但这种看似多元的制度无法保障不稳定的基层劳动者,更多是国家在养老政策上的偷懒。常年来,市场化改革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加剧,体制内外养老金差距扩大,劳动者在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中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负担。养老制度越来越被裹挟、镶嵌在市场中。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历史回顾:从集体互助到割裂无助
承接回顾城市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过去合作社下的集体养老和五保制度,为农村的老人提供了当时尽可能的兜底性保障。而这种保障是通过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生产产品的直接分配来实现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村养老模式重新回到了家庭供养。然而市场经济却加倍带走了农村的剩余产品和年轻劳动力,严重破坏了对老人的保障。新建立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依靠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五保制度,不仅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穷和城乡差距,其本身的保障水平也极其有限。最后,处在农村与城市夹缝间的农民工,要同时面对两个养老金制度的割裂和矛盾。他们实际上承受了最多的不公。
工人养老金的现实与临时账户问题
如果是70年代出生的女工,60年代出生的男工,到了2020年后,他们作为第一代进城打工人,已陆续进入了退休年龄。在他们进城打工的这段漫长的30-40年中,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经过多次变化,所以计算方法也变得极为复杂。缴了十多年社保,退休后能拿到多少退休金?这不光是每一位工友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要了解当下工人养老问题必须知道的背景。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我们以广东省为例进行分析。
而文章后半部分,我们则聚焦临时账户问题。在2010年之后,有这样一群工人,他们已经超过了40、50岁,离开家乡在沿海城市打工了近二十年。他们逐渐在面临着年老、身体机能消退、病痛等困境,养老的问题在他们眼中越来越重要。可是,因为过去社保制度不完善,企业也都习惯不为员工缴纳社保,这导致他们很可能领不到退休金。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场大大小小的补缴社保行动,带着工资单、劳动合同到当地的社保部门投诉自己所在工厂,要求工厂为工人们补缴社保。
在许多行动中,工人们是胜利的一方,工厂补缴了社保,年限足够15年。但是,当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去申请在当地领取退休金时,却遭到了社保部门的拒绝。理由是,他们的社保账户是临时账户,不能在沿海城市当地退休,必须将社保关系转移回户籍地老家,在那里领取退休金。什么是临时账户?这种制度的问题是什么?
现实中工人面对社保制度时的层层障碍
前面的文章梳理了城市和农村社保养老制度70多年的变迁,也指出了目前养老金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但在政策实际的运行中,工人面临着更多阻碍。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连串自上而下的社保改革中,基层工人们的声音基本隐形。社保制度更多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和国家管理的需要,并不是从工人们的需求出发进行设计的。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更是有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违规操作,侵犯了基层打工人的法定权益。
在官方宣传中,养老保险已经基本覆盖了全体中国工人。然而,通过采访调查,我们发现,通过领取社保在退休后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享受退休生活,仍然是绝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遥不可及的梦想。
为什么仍有大量基层工人无法享受社保带来的福利?对于基层工人来说,当他们熬过几十年劳动留下的慢性病、工伤,想要在六十岁、甚至六十五岁后,依靠国家福利,保证老有所依,为什么仍然如此艰难?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本次采访的材料进行了总结,希望可以为读者理解社保制度,提供一些素材。

访谈:流动的青春渴望安顿的晚年
这部分包含了6篇工人访谈稿,他们中有人参与过社保补缴的维权行动,也有人反对缴纳社保。有人目前还在沿海城市打工,也有人已经回老家务农。但共同点是,他们都在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都开始步入老年,也都渴望一个相对安稳的晚年生活,可惜目前来看仍难以如愿。因为每篇访谈篇幅都较长,我们在此只节选了部分内容,请点击“阅读全文”按钮了解各位工友大姐、大哥们的完整故事。
冯姐:一口气干了13年,最后才补缴社保成功
我今年3月开始拿退休金,1100块钱。但就是这1100块钱的退休金,当年能补缴也是费尽了心血。一开始我们找老板谈,找经理谈,谈了好多次,他们都不同意。最后我们就打官司了。每次上法院的时候,我老公都不愿意去,都是老师跟我去。后来看到有希望了,我老公才跟我们一起去打官司。
政府不愿意让我补缴。人才中心、市政府、社保局、市长,他们都不同意,阻碍我、打压我,最后我都把他们都告上法庭了。厂里想阻止我们维权,就说没这个政策。厂里有工会,但是工会都是厂里组织的,厂里给他们开工资,肯定不会给我们这些员工说话的,不会帮我们。我们员工一般不跟厂里上司聊天。
现在回看,觉得有点可怕。哎呀,补缴那个路啊,真长。有时候我在厂里上班,就想,上班这么累,养老保险就快到手了,你还不去补。于是我又请假去补。钱也掏了,律师也请了,路也迷了,要是没有补缴成功就亏了,心里很矛盾很矛盾。
补到了以后非常开心。但他们还不让我在A市退休。我进厂时30多岁,开始交社保已经40多了,所以政府给我们设置的是临时账户,一定要我们转回老家退休。我其实在厂里补缴完都交了13年半了,我后来还买过一年,一共14年半,就差半年,他还强迫我们转回老家补缴,不在老家补缴就不退休。
陈大哥:延迟退休令人难以接受
其实早在五、六年以前,有一段时间就已经在谈这个延迟退休。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核算过,如果实施的话,我是在61.5或62岁左右退休。我是75后,延迟退休政策让我觉得太恶心了。
我说一个很直接的事,就是我们厂里面,像我们同样工种的一些老师傅,没有退休之前死掉的就不少,很多都还在岗位就患了癌症,好多是癌症死掉的。 然后在61岁到63岁之间去世死掉的就占百分之七十。 我们那些老师傅,没有几个老师傅说是退休之后能活到七十、八十,这样的非常少。 长期干这样的车间的工作,身体都不健康,我还是唯一一个在厂里面办了这个职业病保险的。好多师傅,跟我一样身上的毛病,都不知道去找厂里面去办。
现在延迟退休了,对我们来说就是风险。 我现在是做物业,我还能够做到,就是说因为已经是50岁了,再过五年,也许还能够支持五年。 但是真正年龄往60岁去的时候,身体就已经跟不上了。虽然说我有一定的经验,但有经验没精力,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有精力的人,现在都不好找工作。 你没有精力的人,你想怎么去跟别人去拼,实际上拼不了的。
宋大哥:退休不过是多领一笔钱,工作到做不动为止
这些打工经历中,我买社保的时间不算长,刚好15年。以前打工的时候我是没有社保的。2015年那会儿,我曾经在工厂参与过社保维权,最后成功补缴了差不多9年的社保。送外卖的时候,我没有交社保,中断了一段时间。最后做保安的时候,我才重新买了社保,稳定缴纳。两段社保缴纳时长加起来,今年刚好满15年。但现在又有新的消息,缴纳(社保)得满20年才行,也就是说,我还要再买5年。
就按现在的那个规则一直走下去吧。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了也不要想太多的,就打分工,安稳地拿养老、然后退休。我现在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书,一个读大专,一个才刚读高中,也要靠我打工来养家。我也没有按那个新政策具体算过,只知道要买到20年。因为对我来说,十年还有一点远。
至于说退休的开销,如果靠养老金的话,肯定不够了。就打比方,按我现在60岁退休拿的钱,就1800块,那怎么够?我退休了肯定是继续工作的啦。没想过退休了我就要全国旅游,拿着退休金跳广场舞什么的。一般我们打工的都没这个想法,都是做到做不了。所以为什么我没有考虑自己具体什么时候退休,因为没有想过十年后我就可以放松或者放飞自我了,从来没有这个想法的。反正一直做到自己做不动了,一直脑海里面想到都是这样。
所以退休也不算退休,就是多一点钱,就不用供保险了。
王大哥:最早我们都以为社保是骗钱的
我从来对社保不感兴趣。现在觉得社保也没意思,我一直都不交。我老婆说要买社保,我都说我不交社保。现在的工作里有五险,但是没有一金。如果不是必须要买的话,我都不想买养老保险,一直都不想买。我也没有去太了解。以后如果厂里面不给我买了,我就不买。到时候把自己那一部分去退出来就可以了。
要是想领国家的钱,你要等好多年,要交一二十万进去,多久才领得回来,这个账大家都应该会算。我现在存30万固定存在银行里,一直不动。等我老了退休了,哪怕利息少一点,总是有增值的,是吧?人生老病死你都算不到一定的。年龄大的,还能领的多一点,要是年龄小的,根本都是亏本生意。所以我在A市工作了那么多年都没买社保。我理想的政策,是一次性只花几万块钱把社保买断下来,之后就等退休领钱。这样我就觉得压力没那么大。但这是不可能的。国家要交这个本来就是人民的负担。
未来,反正自己能动的时候就会继续做事,不能动了,子女看着办,就这样了。就算是65岁退了休,要是身体健康能做事,我都要做事。你不做事你干嘛?如果身体健康,又找得到事做,就要给子女减轻负担。
但这是假设能找到,现实不一样。现在别说60岁,到了50岁,厂里面卡年龄找不到工作了。我也没办法,这是国家的性质。反正我们贫穷老百姓逆来顺受。国家怎么弄我们就怎么接受,没有去考虑太多它的对与不对,你去考虑那么多也没用。在中国这个年头,你平头老百姓能有什么发言权吗?没什么发言权。
龙姐:拒绝不公,还我社保
厂里分三六九等,当官的有公积金,员工都没有。员工听到当官的都有,就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做事都是员工做出来的,也不是管理人员做出来的。有的人进厂好几年,甚至十年,厂里都没有问过人家愿不愿意买保险。
所以我们就去相关部门咨询,要补公积金和社保。第一批去社保局,我们有9-10名员工。相关部门就打电话问厂里,是不是员工想补缴住房公积金。厂里觉得被投诉了,就报复我们这些员工,说我们去闹事。当时我走在最前面,社保局还把我的身份透露给公司,说我带头闹事。公司把我喊到办公室去问话。我说是去请了病假,他们就问我,怎么请病假去社保局。
我说:“我看到同事们想补社保,我就也想把前面欠的那些补起来。”我其实只差了十几个月,但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差了5-6年,还有一个差了10年。事后,公司经常打压我们,天天都被喊去办公室,天天都拿小脚鞋给你穿。安排工作,然后说这个你做的不对,那个你做的不对,就是找你麻烦,想把你弄走。
还没有罢工之前,工厂说我是带头人,派出所来了七八个人,加上厂里面差不多二十个人,就来抓我。车间的文员给我放信,说大姐你赶紧跑,有人来抓你了,派出所已经在办公室,等下就到车间来。当时我意识到,跑肯定是跑不掉的。我就说,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为什么要跑呢,就留在岗位上工作。
家里人知道事情经过后,很担心。我儿子骂过我,他说“你只有几个月的保险没有补,去闹什么闹,闹能得到多少好处。”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参加的行动,把自己的权益找了回来,我问心无愧。
刘姐:社保费用年年涨,不知何时能缴够
刘姐回家的第一年缴了社保9700多,到今年就涨到了11000元,这对他们一家来说是种沉重的负担,大部分费用要靠子女来承担。当子女听闻刘姐每年还需要缴如此高昂的费用时感觉难以理解,但缴了几十年的保费如今放弃更是于心不忍。连年上涨的社保、医保费用让刘姐颇感不满,她说“医保也不好用,今年医保又涨了两三百,以前用医保还能领米领油,现在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多缴的钱去哪了”,“我觉得社保最大的问题就是费用,年年都在涨”。刘姐介绍说,她的儿子也曾考虑过缴纳社保,但延迟退休、延长社保缴费年限的政策落地,而且到年龄又领的少,让他们感觉参加社保不划算,打消了这个想法。
领着养老金,跳着广场舞、吃完饭散步的生活是刘姐的理想。目前,刘姐的日常开销还要靠务农、子女的收入来维持,所以她只能在干完活之后满是羡慕的看别人跳舞。刘姐说等缴满15年,她每个月可以领1100左右,但在生活成本逐渐攀升的背景下,她觉得之后也可能还要干些农活来维持生活。
如今,和刘姐一起打过官司的工友,为照顾生病的母亲也回了老家,他们失去了联络。曾经电子厂的老板将工厂租了出去,在A市又新开了公司,孩子也都在加拿大定居。
专题之后,我们的思考
这部分是本专题参与者们在访谈之后的思考。这些思考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们写作的灵感,但更多的是尚未解决的困惑、对未来的判断和来自于现实的情绪。在访谈工人的过程中,我们一点点察觉到这个议题的沉重与艰难。但这些言语中所能透露的,相较于工人面对的残酷现实,也显得微小而轻薄。
虽说我们还年轻,养老看似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然而,随着访谈的深入,它逐渐变得真实而迫近,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课题。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折射出的不仅是老去之后的难题,更是当下每一位打工者生存的困境,揭示着不公的经济生产制度和深埋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
每一次,当我们试图为工劳小报的分析找到一个结尾时,我们都会面临相同的难题:我们不愿将结尾停留在政策建议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建议在当下不可能被真正施行,我们也不是体制的修补者;我们也不愿陷入无尽的无奈与痛苦中,那只会让分析坠入深渊,徒增无力感;我们更无法将结尾收束在空洞的行动号召里,因为缺乏有效的路径与方法,呼吁如同微光坠入深海。于是这一次,我们将结尾收在这些参与者的思考中。
我们希望这些零碎的思考,以及以上所有的文字,能为读者和未来的劳动者启蒙一种行动意识。这种行动意识,也许是使我们从未曾重视过社保和养老,到开始关注自己已缴或者未缴的社保,衡量自己的职业状况是否稳定以及是否能保证未来可以领到可观的养老金额。也许是更大胆一些,开始跳出现有制度的限制,反思其和经济体制的深刻联系,不再仅仅追求改良。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企业随时裁员和倒闭、养老基金走向枯竭、政府延迟退休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意识尤其重要。哪怕我们依然困惑,但我们依然有改变与行动的企图。
龙姐提到,她的一名工友成功补缴了社保,但因为补缴时已超40岁,只能办临时户口,现在到了退休年龄仍领不到养老金——尽管这名工友补缴后起始年份实在40岁之前。冯姐说,她也是这种情况,在打工的地方只给办临时户口,她回老家后又在老家交了一年保险,现在可以在老家退休。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各地临时户口的政策不一样?还是她们老家的规定不一样?还是政府故意让有些人补缴成功、有些人失败,让本应白纸黑字的规则变得模模糊糊?
龙姐提到她儿子不想交社保,觉得这是“打一辈子工”的人才需要的,自己不想一辈子打工。这样的想法似乎在新一代工人中更加普遍,可能也是很多年轻人不想交社保的原因。这样的想法会让年轻人对自己劳动权益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我在意的主要是工人的生命的消耗。退休金政策是为了保障工人晚年生活,这都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工人可以活到老年,有一段退休能够安养的时间。但事实上更令人难过的事实是,许多工友在前30年的打工生涯中就已经过度消耗了身体。职业病、工伤、以及更多难以被认定的慢性伤害都在提前透支工人的生命。这让大部分工人无法活到一般意义上的老年。
在中国,养老金除了是一种社会保障外,也更像是对于前20-30年在缺乏劳动保障环境下辛苦付出劳动的工人的历史赔偿。但是,迟至2010年左右才推出的社保政策、延迟退休、临时账户、缴费年限的限制,实际上都是在逃避社会/国家对工人养老的责任。不断提高获得养老金的门槛,不断延迟获得养老金的年限,让这种“赔偿”也变成空谈了。所以社保问题,我觉得本质上不是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而应该是一种历史正义问题,是关于工人的付出如何被回报的问题。
社保是一种对于工人来说是缺少的东西,而不是他们享有的多余的东西;就像对于奴隶来说,自由身不是加到他身上的一种恩赐,不过是归还了本来属于他却被剥夺了的东西。过去,自由人的诞生给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制创造了条件;现在养老金是什么呢?是用一份三十年、四十年后才产生效力的不平等条约,却在当下每月定额地从劳动者的工资里抽出一份来,等到他们有那个幸运熬过几十年劳动留下的慢性病、工伤,撑过缩水的预期寿命,再从不稳定的基金里发放些残羹剩菜,以此让他们能留在岗位上。
我觉得作为政策的养老保险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笔迟发给劳动者的工资,这笔钱不来自其他地方,正是来自劳动者自己。这一点来说,各个基于自由市场、雇佣劳动、私有制的国家的退休金,对于劳动者来说能起到的养老保障作用都很有限,最后拿到的数额不足以保证一个有质量的退休生活。只不过国内混乱的地方政策、糟糕的基层执行,以及专制官僚化的顶层治理,使得劳动者哪怕想要稳定地走完社保过程最后拿到这笔“迟发的工资”,也困难重重。劳动者的叙述也证明了,养老金就是多拿一笔钱。想要支持自己年老后的生活,更多靠的是子女、存款这些家庭化的抚养,如果家庭也没有富余的能力,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出卖自己劳动力,直到生命力完全枯竭。
现行政策是可以修订的,基层的执行也是可以监督完善的。但是反思作为整体制度一部分的养老保险时,我们必须大胆地去构想一个超出福利资本主义框架下,对劳动者退休生活保障的可能性。事实上,哪怕是资本主义西方的退休保障也远远不是仅靠“养老金”的(链接):会员制的养老服务机构、自治形式的退休社区、医养结合,加上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这并不是在指示走向商业化、市场化养老,而是揭示了养老的社会化本质。劳动者的养老不只是一笔比例确定的返额。它不仅和医疗、社区还有科学技术的进展离不开,难道可以脱离劳动者年轻时没有罢工议价权、没有自主的工会、没有政治生活、甚至没有社会关注的整体现状,来空谈尚且浮在空中楼阁的养老金吗?
仅仅指望在现行的官资同流合污的体制下,通过对社保、养老金政策进行修修补补,来使劳动者获得有保障、有尊严的退休生活;就好像幻想在议会里为工人赢取多数票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我觉得,改开前的历史向我们展现过的另一种可能性,和最新的无耻的延迟退休政策,都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击穿了这种幻想。
在宋大哥的口中,愿意维权的工友和劳工机构在维权抗争中缺一不可。在工人们维权的时候,机构为工友们提供免费的劳工权益宣传和法律服务,将大家凝聚在一起。虽然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可能与工人们素不相识,但在关键时刻会被众人寄予厚望。就像宋大哥说的,相比于他们这些有过抗争经验的工人来说,劳工机构的帮助更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和信服。机构会将工人们的个人维权凝聚在一起,形成集体维权的力量,才更有可能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从这次访谈的经历以及其他的文献可知,至少在十年前,劳工机构并非非法,相反还引起了一部分政府的注意,并推动了部分地区政府将工人服务市场化,当地政府和官方工会与劳工NGO形成合作,有效的推动了资本与劳工的矛盾在相较温和的过程中解决。
但至少就当下看来,温和的渐进式改革似乎已经失败,参与过推动集体协商和维权行动的组织,不管是温和的劳工服务机构被相继关停或者污名化,还是激进的工人学生运动被直接镇压,以及现在更为罕见的劳工机构和数量并没有减少的工人维权抗争运动。非官方劳工运动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是否证明了一味迎合政府合作走市场服务化的方式在当前背景下是不可能成功的呢。如果大环境不改变,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吗。
在社保问题上,接触过的工友大都是老一辈的,虽然不一定对社保有完全的概念,但基本都知道这是一种福利政策。话虽如此,没有任何一位工友确实因为社保而安心并“退休”,也没有人真的认为靠社保就能覆盖生活中的所需,另一方面,接触过的工友也没有“正常”拿到社保的,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维权。由此可见,社保作为“保障”的维度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事实上,社保作为“退休工资”的替代是完全不匹配的。因为“退休工资”是退休制度的一环,而我国的退休制度早期和单位制基础设施建设密不可分。换句话说,退休待遇中的一部分保障本就是非货币化的,但社保却是以单纯货币形式结清了单位、社会、国家对劳动者的所有赡养义务。即使社保的货币金额和退休工资相当,那种保障性的基础设施也已经一去不返,实际上养老是更艰难了,保障是更缩水了。对于工友来说,钱不够用是一回事,老了“哪里都要用钱”却是另一回事,社保存在制度上决定性的片面化,绝非个别ngo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因而一些工友感到无助,社工感到无力,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归根结底,我们不可能指望靠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去覆盖基础设施缺口,其性质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实际是差不多的。而一旦为了覆盖基础设施缺口而开始资本化运营,又没法解决货币要求了。
可以说,“退而不休”将是很多劳动者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社保基金存量与来源的双重萎缩让人显著感觉到社保制度的崩溃趋势,对于未来养老的期待和指望越来越不能寄希望于这一制度。如此一来,许多年轻劳动者不想交社保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交上去的钱不见得就能在未来真的保障自己的生活,但眼下生活里就是需要钱的。一些认识的劳动者将社保戏称为“第二税”,实际上就是对社保究竟能不能保到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名义上说,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如今社保也具有相同的名义,却越来越显得和税一样像一种不透明的转移支付手段,在等差极大的不同退休金支付标准下(不同等级间、不同地域间、不同单位间、稳定雇佣与不稳定雇佣间),“社保”给付的部分究竟多大程度上匹配于劳动者被抽取的部分?基层劳动者究竟多大程度上变成了高食利群体享用的红利?这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令人不平的点正在于此——当许多劳动者冒尽风险,吃尽苦头,花尽时间争取到了购买社保并获得给付的资格,这一资格却逐渐显得像是一种吃剩饭的资格。
通过此次访谈,深刻体会到一线劳动者的综合保障是个大难题,我所采访的是通过抗争争取到一部分权益的工人,即使是这样,退休后的生活仍然是够不到其理想化的生活的。而我很清楚,像大姐这样“斗赢“的工人其实还是少数,大多数工人劳碌一生最后其实是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他们不得不在本该退休的年纪继续找活干,而年纪越大越难找工作,能找到的工作反倒是不适合年纪大的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大姐年轻外出务工,中年几乎一直在为养老保险去奔波,打官司、上访,争取到权益时人已经快步入老年,她的人生就是一部抗争史,与这残酷不公的世界抗争。在大姐描述自己的斗争故事中,大姐透露出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年轻工人和大龄工人的思想冲突,年轻工人想赚现金不在乎社保,大龄工人在意社保,因此斗争中参与的几乎都是偏中大龄的工人。二是由于“流程化”导致维权的每一步都繁琐且漫长,许多人不得不为了生活去赚钱糊口,时间精力被消耗,没有一开始高涨的维权热情,很多人半途而废。三是队伍中有为了蝇头小利出卖同工的工贼,不知拿了这些老板什么好处,将维权的队伍和核心人员的一些情况出卖给政府,让本就艰难的斗争失去外部的机构和其他势力的帮助。
听完大姐的话深感人生之艰难!
访谈:贝果、天线、超级64、马乙己、hachiware、烤鸡腿、橄榄叶、Xay
写作:贝果、天线、烤鸡腿
编辑:向日葵、烤鸡翅
在最后
以上是本期工劳小报特刊的全部内容。我们正在探索将日常的工人资讯定期整理为 Newsletter,希望你可以来信([email protected])提出建议或加入成为志愿者,同时也请你多多分享给墙内的朋友们。点击下方按钮可以订阅和阅读往期内容。